来源:纵横杂志
卢光琇 纵横杂志
2024年06月24日 20:56 北 我1939年4月出生在湖南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良好的家庭氛围,使我对事业有一种矢志不渝的追求。我从事的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以及人类胚胎干细胞应用研究,通俗地讲就是试管婴儿与干细胞研究。党和国家给了我很多荣誉,我曾任全国政协常委、湖南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湖南省委主委等职,但我一生的梦想是继承我父亲——中国医学遗传学奠基人卢惠霖教授未竟的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积极性优生而奋斗。本文讲述的是我40年从事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试管婴儿)研究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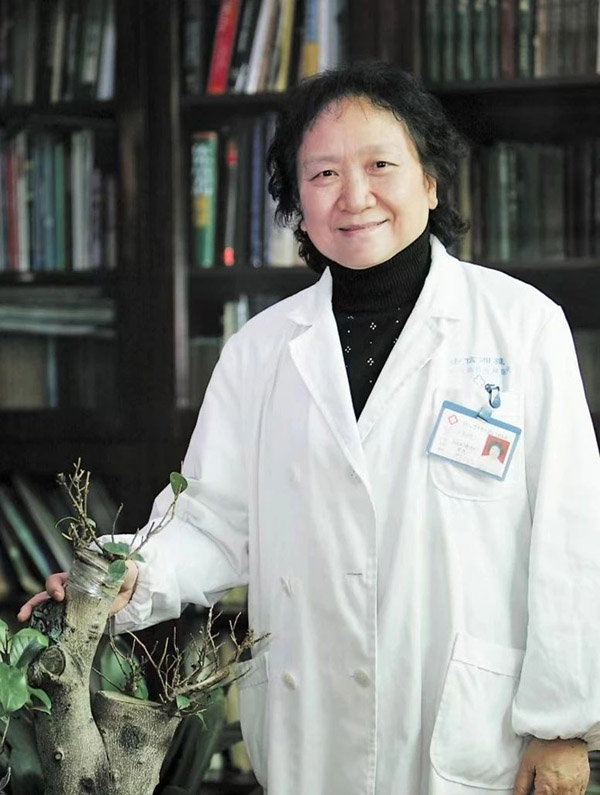
卢光琇
父亲对我的影响
在我的一生中,父亲是对我影响最深的一个人。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研究,在中国可以说已经进行了70 年,父亲做了前30年,我按照他的指引做了后面的40年。我所有的成绩,都是站在父亲的肩膀上取得的。父亲的一生,经历了无数波折和磨难,但每一次他都坚定地挺了过来。他对我在科研事业上最大的影响有两点:一是对理想坚定不移的追求,面对困难决不低头;二是要懂得感恩。
我的父亲卢惠霖是湘雅(湖南)医学院教授,1900年9月3日出生于一个笃信基督的宗教家庭。1925 年,父亲漂洋过海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动物学系深造,成了享誉世界的著名实验胚胎学家、细胞遗传学创始人摩尔根和著名细胞学与实验胚胎学家威尔逊教授的门生。他也是在这里开始了独立的细胞学研究,并首次在低等植物蕨类的孢子母细胞中发现了一种典型的亲锇小体。然而,这一研究刚刚起步,父亲就被无情的肺结核杆菌击倒了。10个月后,饱受疾病折磨和思乡之苦的父亲毅然放弃了即将进行的博士论文答辩,谢绝了导师和友人的挽留,于1929 年抱病踏上了归国旅途。
长沙沦陷后,父亲扶老携幼,随着任教的雅礼中学从长沙逃往沅陵,后又接受湘雅医学院院长张孝骞的聘请,从沅陵到贵阳,加盟湘雅医学院教师队伍。再后来,又随湘雅医学院师生逃难到重庆。一路颠沛流离,母丧妻病,4 个女儿嗷嗷待哺,苦不堪言。
经过十四年抗战和三年内战,终于盼来了湖南的和平解放,也把陷在深渊中的我们一家解放了出来。年近半百的父亲夹在湘雅医学院的学生们中间,挥舞着彩色小旗,欢天喜地敲打着脸盆饭碗迎接解放军入城。历经近20年的战乱漂泊,父亲深知和平与安定的来之不易,于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学校工作与社会公益活动中去。特别是通过对国人身体素质与遗传学的研究,“生一个健康的孩子”这一优生学的核心理念在他心间扎下了根,成为他一生的追求,并延伸到了我的生命里。
20 世纪70 年代,尽管历经各种风波,父亲在医学遗传学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并带动我国医学遗传学整体水平的快速前进,科学界公认他是中国医学遗传学的奠基人之一。那个时期,因为各方面条件有限,怀有遗传性疾病胎儿的妇女,要么在妊娠时期自然流产,要么生下来才发现孩子有异常,影响孩子终生。能否有一种积极性优生的方法,在胎儿甚至更早的胚胎阶段就能判断胎儿是否存在异常?这成为他日夜苦思的问题。1978年,当英国诞生第一例试管婴儿的消息传来,已是78 岁高龄的父亲立刻感受到,他一直苦苦寻求的积极性优生有了可实现的途径,那就是通过试管婴儿技术,人类可以在更早的阶段应对遗传学疾病的困扰。
在父亲的著作《人类生殖与生殖工程》一书中,他首次对人类生殖工程的未来发展作出规划,提出了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研究”到“将辅助生殖技术和遗传工程相结合的研究”,再到“在配子和胚胎水平进行遗传学改造的研究”的“三步走”战略。对这三个阶段的研究规划,可以说覆盖了我们生殖遗传研究的整体脉络,成为我们此后数十年求索中不灭的灯塔。
当时父亲已年近八旬,为照顾父亲,我从广东梅县回到长沙,在湖南医学院从事局部解剖与外科手术学教学。此前,我先后在衡阳人民医院、梅县“黄岗医院”担任外科医生,在业内小有名气,人称“湘南一把女刀子”。
有一天,父亲突然问我:“卵子该怎么取?”多年的外科经验加上当时知识所限,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开腹取呗。”父亲听后暂时没有回应。我非常好奇,父亲为何突然提出这样的问题?追问下才得知,他想做试管婴儿,想要取到卵子和精子,在体外受精。
这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事情,我听后非常震惊。但看到父亲严肃的样子,我知道这不是开玩笑,他是经过认真考虑并且有着强烈的决心的。当了解到父亲提出的在中国开展人类生殖工程研究的积极意义,我立即被他的暮年壮心所感动,主动提出要为父亲分忧解难。我试探着问他:“让我来,能行吗?”父亲听了十分欣慰,但没有马上答应,他说:“你以前从事的是外科,现在从事这样一个全新的领域,会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你自己不但要做研究人员,还要做技术员,甚至要当工人。”但我已经考虑到了这些困难,甘愿为这项事业奉献力量、作出牺牲。父亲考虑几天后,终于答应了我的请战。就这样,在父亲手把手的指引下,我正式转行,投入到了人类生殖工程研究中。
哭过、累过,但始终执着
1979年,父亲将对生殖遗传领域还一无所知的我送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进修。拿惯了手术刀的我,开始尝试洗试管、倒烧杯这类的工作。
当时,父亲曾接到一位患者的来信:“卢教授,您是有名的遗传学家。现在我没有精子,不能生育,咱们国家有牛精子库却没有人精子库,为什么您不能做人的精子库呢?”已步入耄耋之年的父亲那时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于是他将这封信转给了我,我考虑了一下说:“我们可以做。”
接下来,在一位老师的带领下,我骑着单车在颠簸的土路上走了两个多小时,来到北京郊区的牛精子库。我是奔着建立人类精子库的目的来的,我把在这里看到的所有细节都记录在了本子上。三个月后,我揣着一本厚厚的冷冻牛精液的学习笔记,回到了父亲身边。

1981年卢光琇教授(右)指导助手进行精子解冻
创建精子库的过程是异常艰难的。中国一直以来都是思想比较传统的国家,人们对于优生学、遗传学尚且存在许多误解,更别说建立人类精子库了,人们简直是“谈精色变”。随后,我们出现了没有场地、没有设备、没有经费、没有人员等一系列状况。鉴于此,我只能敲开学校一个又一个实验室的门,“化缘”一样讨要试管、烧杯以及人家闲置的仪器,在办公室用布隔开一方小天地,组织了一个近10 人的试验小组。
试验小组是有了,然而精子库最关键的试验品——人的精液,却始终没有着落。我们研究组里有三个男老师,却没有一个人愿意主动捐献精子做实验。没办法,我只能求助于我的丈夫。没想到他非常支持我,排了一些精子给我。当我把这些精子拿到实验室,那几个男老师纷纷凑上来问:“卢老师,你哪里得来这么好的精子?”我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这是我先生的。不像你们三个大男人,都不献精。如果我有,我早就捐献了。”他们三人听后十分羞愧,此后我们实验室再没有缺过精子了。

1983年卢光琇教授(右一)构建的早期改良冷冻精子库
精液有了,前期准备工作也差不多了,我的研究工作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现在的精子都是在零下196℃的液氮中冷冻,但当时我们没有见过液氮,后来通过别人介绍,才好不容易从一家工厂要到了一小罐。把精子放进液氮罐后,我和同事就守在旁边,一晚上都没敢合眼,生怕罐子一不小心就爆炸了。等到第二天天亮我们从罐子里取出精子后,高兴得蹦了起来。我们还自制了一种冷冻精子保护剂。记得在等待冷冻精子复苏的时候,我们整个研究小组人员的眼睛都一直盯着恒温箱,静待着激动人心的时刻。然而,当我们满怀希望地从恒温箱中拿出装有精子及保护剂等的器皿时,大家都惊呆了:这明明是烤蛋糕呀!原来,用报废的旧设备改成的恒温箱,恒温计失灵了。
1981 年10 月,我们终于成功了,冷冻精子的复活率达到了10%。这一重要成果,坚定了我的信心。一个月后,精子复活率提高到了40%。一直关注着此事的湖南医大领导也伸出扶助之手,在紧张的科研经费中挤出一部分给予我们支持。
1981 年底,我国首家人类精子库、国家人类精子库的前身——湖南医科大学人类精子库,正式宣告建成。随后,我约来了那位曾经给父亲写信的无精患者。最终,患者的妻子于1983 年诞下了我国第一个人工授精婴儿,人类精子库开始在临床应用中逐渐显现其效用。
消息传出后,我们收到了无数来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肯定及表扬,但也有许多人不理解,甚至辱骂我们,说我们建立精子库、做人工授精,就是把人当畜生搞。但我义无反顾,始终坚定地继续着自己的事业。
精子的问题解决了,但做试管婴儿还需要卵子,可卵子不像精子那样可以轻易地得到。为了能找到卵子做实验,我抱着一个用热水壶和温度计自制的“恒温罐”,守在当时学校附属医院妇产科手术室外,希望医生能给我一些病人废弃的卵子。刚开始这些医生还算客气,但见我待得久了,他们逐渐厌烦,甚至都不正经看我一眼,只想把我赶出去。连续守了很多天却没有得到一个卵子,还遭受了无数白眼,我委屈地跑到父亲那里哭了一场。父亲看后非常心疼,马上给学校打了电话,手术室的人这才配合,给了我做实验的卵子。就这样,我们一点一点摸索、一步一步克服困难,将实验不断推进。
这期间,我们还得到了湖南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20世纪80 年代初,时任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看望我父亲,问父亲有什么要求。父亲没有提任何个人要求,只希望省里能支援20万美元用于人类生殖工程研究。那时“文革”刚刚结束,20万美元无异于天价,但毛书记马上答应了。不过他说,省里也比较困难,先设法支援10 万美元,其余要等下次税收后才有。这句话让我倍感震惊,这时我才明白,我手里的经费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于是我暗下决心,一定不能辜负湖南省领导以及湖南人民的期望,一定要将这项技术搞成。
1985 年,当试管婴儿研究被列为国家重点“七五”攻关项目之后,我每天基本上都是在试管婴儿实验室里度过的,吃饭都是家人送的,有一餐没一餐,导致经常胃痛不已。有一次,为了连续观察胚胎的体外发育,我在实验室整整待了三天三夜,胃痛得倒在了地上仍不愿离开,后被同事和学生强行抬到手术床上休息。但到了观察时间,我又按着肚子起来观察。回想起那段日子,真是着急得不得了,因为实验老不成功。用了那么多的钱,却还是没有个结果。我父亲之前说过:“不看到试管婴儿出生,我死不瞑目。”那些长辈看到我也说:“光琇,你要努力啊,你一定要给你爸爸争气啊!”好在利用这10 万美元,我们不仅购置了需要的各类仪器,还把我送到国外大学学习深造,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及经验。记得当时回国时,别人都是带各种各样的特产、礼品,而我提的是各种仪器。但在实验过程中,无论怎样操作,结果都是失败,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到最后我才发现,问题的根源在于培养胚胎的水质不达标。最后,通过联系国外校友,我们终于得到了更加纯净的水,实验终于成功了。
经过艰苦的八年努力后,1988 年6 月5 日,湖南省第一例试管婴儿呱呱坠地。两天之后,我国第一例供胚移植试管婴儿出生。试管婴儿研究,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那一刻对我而言,真是百感交集,如释重负。父亲的期许、国家的信任、团队的坚持以及10 万美元老百姓的血汗钱,在那一刻终于得到了回应。

卢惠霖教授抱着中国第一例供胚移植试管婴儿罗优群
父亲如愿以偿地见到了中国的试管婴儿,他把小婴儿深情地抱在自己怀里。这历史性的一幕被拍成照片,挂在现在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三楼的候诊厅里。我至今都很感慨,没有父亲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后来所有的研究都是在他的框架下进行的。我最感欣慰的,是让他在有生之年看到了中国试管婴儿的诞生,我没有让他失望。
一纸禁令,研究被迫中止
20世纪90年代初,因为政策原因,我们的临床研究被迫中止(有人认为我们的研究与计划生育政策背道而驰)。无奈之下,我只能沉下心来做基础研究,开展大量动物实验,并将手中的技术成果用于其他遗传优生领域。
当时,在湖南张家界有个远近闻名的“傻瓜村”,全村500 来人,呆傻率达27% 以上。我开始以为是遗传方面出了问题,于是在原卫生部妇幼司建议下,带领6 个专题调研组进村调查。经过1992—1994年三年时间的调查,我发现“傻瓜村”的“罪魁祸首”并不是遗传病,而是当地缺碘引起的克汀病。我将调查报告分别寄给国家民政部和中国残联。没想到在党和国家的重视下,该调研成果成为1994 年国务院启动全民食盐补碘的科学依据之一,国务院更是确立1994 年为“补碘年”,此后大规模流行性群发的克汀病在中国基本消除。
1989 年,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建议我将试管婴儿技术运用于熊猫繁殖研究。同年,我与四川卧龙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协作开展“大熊猫生殖生理及人工繁殖新技术研究”科研课题,成功诞生双胞胎大熊猫,为破解国宝繁育难题作出贡献。
虽然这段时间我们不是直接从事试管婴儿研究,但是我仍然坚信,辅助生殖与遗传技术的春天终会来临。我带领着自己的团队,默默地进行着各项技术攻关。1990 年,中国第一个植入前胚胎遗传学诊断动物模型建立;1991 年,国际上第一例经畸形精子分离术治疗后诞生的正常婴儿诞生;2000 年,中国第一例经超快速冷冻后的冻胚移植试管婴儿诞生。在辅助生殖技术受到时代限制的背景下,当时的钻研与探索为后来辅助生殖技术与遗传技术的结合留下了火种,奠定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我们在人类干细胞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在进行生殖遗传的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再生医学是为解决人类面临的主要难治性疾病和健康威胁而创立的医疗技术,是人类健康长寿的希望,也是国际医疗界重点发展和研究的高科技医疗领域,其发展将引起临床医学的革命,其核心是干细胞技术和治疗性克隆。
治疗性克隆胚胎干细胞技术,是通过核移植技术,将患者体细胞中的细胞核通过显微注射方法,送到已经除去核的人卵细胞(即卵壳)中。当时学术界普遍认为,人体细胞在分化过程中,由于高度分化而失去了再分裂能力,并最终会衰老死亡。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其实机体在发育过程中已在早期胚胎、骨髓、脐带之中保留了一部分未分化的原始细胞。这些未分化的原始细胞只要经过特定的诱导分化程序后,即可以不断自我分裂、生长出成人体内200 多种作用不同的细胞,并进而发育成肌肉、骨骼、神经系统等组织和器官。这些细胞可供移植使用,用来治疗许多疾病,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如,由于胰岛素分泌细胞受损而引起的I 型糖尿病,就可以通过移植胰岛素分泌细胞来重建胰腺分泌胰岛素的功能。这将引起医学治疗的一次革命。
1996 年,我们团队培育了国内第一批核移植小鼠。1999 年,我们在国际上首次建立了人类体细胞克隆胚,这项技术较美国整整早了两年。在此基础上,2000 年,我们发明了先注核再去核的新方法,获得世界上首个人类治疗性克隆胚胎。2001年,我们又成功分离培养出了人类胚胎干细胞,并建立了4 株人类胚胎干细胞系,进而建立了干细胞库。2002 年9 月,Nature杂志发表了题为《中国:干细胞在东方升起》(China:Stem cells rise in the East)的文章,介绍了我们项目组为获得干细胞而建立治疗性克隆胚的研究成果。2002 年3 月,美国《华尔街日报》作了标题为《当西方还在纠缠于伦理争论时,中国已经在干细胞领域遥遥领先》的整版报道。2002 年5 月,英国《泰晤士报》作了题为《中国领跑人类克隆研究》的报道。2003 年,我们又获得了首个治疗性克隆囊胚,核移植囊胚发育率达13.3%。这些成果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新加坡《海峡时报》、法国电视五台、德国《法兰克福报》以及我国台湾《联合报》、香港《东方日报》《文汇报》等媒体均给予关注。
不得不说,真的需要感谢那段时光。虽然辅助生殖事业受到了政策的限制,但却给了我们更多的时间去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这也为我们之后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联手中信 快速腾飞
在试管婴儿技术取得成功后,我在湖南医科大学(今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组建了以研究生教育为主的人类生殖工程研究所,取得了一系列成绩。然而,由于当时高校科研经费不足、相关体制机制不清晰等客观原因,团队的许多科研成果无法广泛应用于临床,这让我和我的团队感到十分焦虑和困惑。
但我们没有屈从于现状,而是作出了走产学研一体化道路的突破性决策,为“中信湘雅”模式的创立奠定了重要基础。在中南大学的支持下,我们以研究所名义成立了不孕与遗传专科门诊部,不少患者慕名而来,科研经费的燃眉之急得以暂时缓解。但随着患者越来越多,小小的门诊部不堪重负,发展后劲严重不足。
2002 年,时任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回到湖南,希望投资具有潜力的医学项目。在反复考察无果后,他与中南大学首任校长胡冬煦一同与我的团队会面,听取了人类辅助生殖产业发展介绍并参观了门诊部。王军董事长敏锐地意识到,人类辅助生殖是高科技朝阳产业,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经过反复论证和考量,中信集团决定为我们的辅助生殖事业提供资金支持,由中信医疗健康产业集团、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和我们科研团队合作,共同组建“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
通过一系列体制创新,中信湘雅成功摆脱了体制束缚,经营管理的各项工作得以高效落实,发展动力得以充分释放。从2012 年8 月开始,医院与华大基因合作,诞生了世界首批经大规模平行测序技术的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 筛查试管婴儿(PGD/PGS)。2013年7月8日,我在英国伦敦举行的“欧洲生殖医学年会”上报道了这一成果,得到国际的广泛认可。2010年,医院引入“肿瘤生殖遗传学”研究,通过PGD 技术阻断遗传性肿瘤疾病在家族中的蔓延,并于2015年先后诞生两例“无癌宝宝”,为这类患者健康生育带来了福音。2016年,医院诞生了首例经MicroSeq排除染色体平衡易位的健康宝宝。2019 年,医院“试管婴儿”治疗超5.2 万个周期,平均临床妊娠率达62.3%。截至目前,经医院助孕出生的婴儿累计超过16 万个,为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作出了积极贡献。2017 年8 月,英国Nature杂志报道,我们医院一年辅助生殖治疗周期相当于美国的1/4。我们的精子库目前已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精子库,精子库存约15万份,累计为30 余个省市的60 余家生殖中心提供优质精子来源。
与此同时,我们在人类干细胞领域的研究也驶入了快车道。2004年4月,国家发改委批准组建人类干细胞国家工程研究中心。2005年,我们获批组建人类干细胞国家工程中心。这是湖南省生命科学领域唯一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以及国内首批基因检测技术应用示范中心。依托这一平台,我们构建了世界首个人类体细胞克隆囊胚,引发《泰晤士报》《华尔街日报》等整版报道。2006 年,我们获国家“863 计划”资助,建立了人胚胎干细胞资源库,并在全世界首次证实“干细胞库建设是解决干细胞临床应用免疫排斥问题的重要途径”。
现在,人类干细胞国家工程中心已建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世界规模最大的人胚胎干细胞库,库存525株人胚胎干细胞系,为再生医学提供丰富的种子资源。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们团队主动向省里请缨,捐赠临床级别MSC 制剂300份,用于重型/危重型患者救治及恢复期患者肺纤维化治疗。救治的重型患者无一例转为危重型,全部治愈出院;两例危重型晚期ECMO 治疗患者也治愈出院(包括全国首例采用清醒ECMO治疗并成功撤机患者)。我们和长沙市一医院共同成立恢复期肺纤维化患者干细胞治疗小组,免费提供干细胞和多种检测和服务,已完成多人治疗,得到患者的高度评价。
因为在医学、科学、教育等领域的一系列努力,我们团队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973 项目、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中华医学会基金会(CMB)等多项课题资助,先后两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本文选自《纵横》杂志2021年第2期“纵横视点”栏目,文字略有删改,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
信息提供:张志国(《纵横》杂志)

|